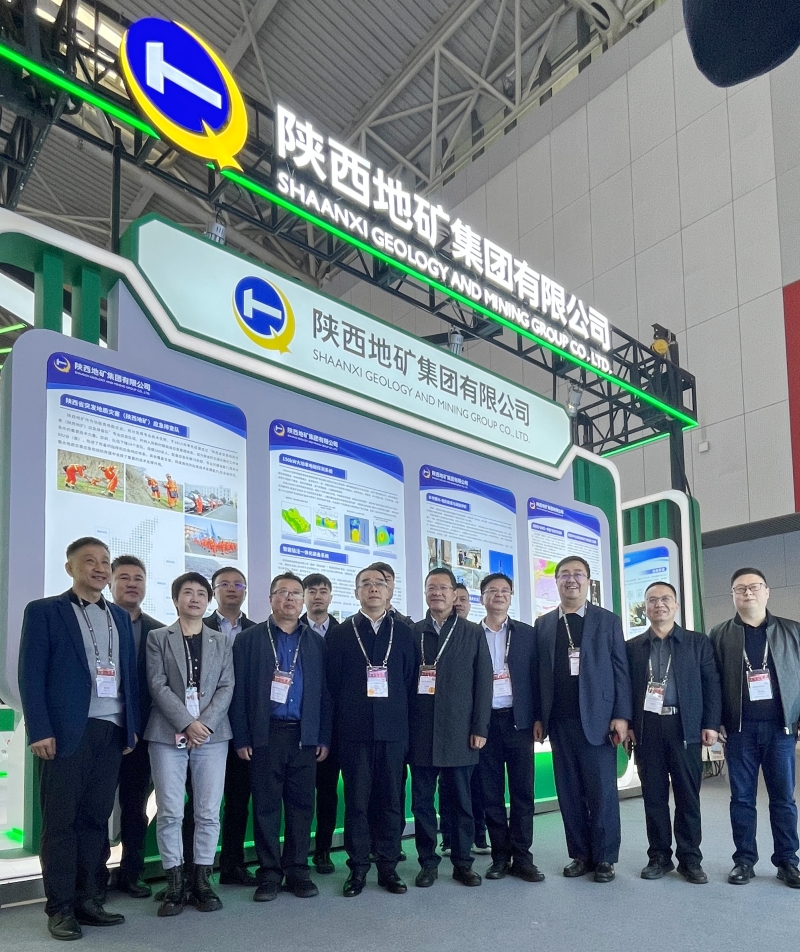民國(guó)時(shí)期的地質(zhì)先行者
——《荒野上的大師》中的地質(zhì)先輩
在中國(guó),地質(zhì)學(xué)家李四光的名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,而作為地質(zhì)行業(yè)的第三代子弟,從小到大耳濡目染了地質(zhì)隊(duì)員常年駐守野外的工作模式,想當(dāng)然的以為我們的行業(yè)一直都是這個(gè)樣子的。直到讀了亞洲卓越新聞獎(jiǎng)獲得者、國(guó)內(nèi)一流的紀(jì)錄文學(xué)大師張泉先生的著作《荒野上的大師》,才知道了民國(guó)時(shí)期的丁文江、翁文灝、謝家榮等地質(zhì)先行者的名字,才知道了習(xí)以為常的田野地質(zhì)工作原來有這樣傳奇的來路。
整本書的內(nèi)容看起來感覺“熱辣滾燙”,我一次次忍不住淚目,在書中記下無數(shù)標(biāo)記與感嘆!民國(guó)混亂又苦難的背景里,一個(gè)個(gè)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從那個(gè)塵土飛揚(yáng)的年代活生生地走到了我的面前。蔡元培、梁?jiǎn)⒊ⅠT熙運(yùn)、張伯苓,這些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,竟然都幫助過民國(guó)時(shí)期的“地質(zhì)調(diào)查所”。而我們語文課本里的“熟人”魯迅先生首先正經(jīng)學(xué)的是開礦。他和同學(xué)合著的《中國(guó)礦產(chǎn)志》還是當(dāng)時(shí)國(guó)民的必讀書。回望20世紀(jì)初的中國(guó),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還是一片待開墾的荒野。在兵荒馬亂的戰(zhàn)爭(zhēng)歲月里,卻有一大批科學(xué)工作者,在吃穿用度什么都是重重困難、連生命都岌岌可危的亂世,用中國(guó)科學(xué)人的錚錚鐵骨在世界上硬剛出了中國(guó)人的科學(xué)成就。
翁文灝的《地質(zhì)學(xué)講義》、謝家榮的《甘肅玉門石油報(bào)告》《石油》、丁文江的《中國(guó)礦產(chǎn)志略》,地質(zhì)學(xué)的一系列學(xué)術(shù)成就在內(nèi)憂外患、國(guó)土淪喪之際先后粲然出世,在侵略者極盡所能的抹黑我中華歷史、否定我中華文化、貶低我中華兒女血脈之時(shí),一介書生用瘦弱的雙肩扛起了民族尊嚴(yán),向世界證明“我們絕非下等民族”。
丁文江從英國(guó)學(xué)成歸國(guó),面對(duì)中國(guó)地質(zhì)調(diào)查幾乎一片空白的狀況,背起地質(zhì)錘、羅盤和放大鏡,獨(dú)自一人深入山西、云南、貴州、四川等地的崇山峻嶺中,進(jìn)行動(dòng)輒數(shù)月經(jīng)年的地質(zhì)考察,行程幾萬里全靠一雙腳。他以近乎苦行僧般的研究方式,留下了中國(guó)科學(xué)家系統(tǒng)田野調(diào)查的第一串腳印。
地質(zhì)先輩于亂世荒野之中培養(yǎng)起了中國(guó)第一代地質(zhì)人才:李四光、謝家榮等都曾跟隨丁文江在野外摸爬滾打。他們的田野研究之路,渾身泥濘、狼狽不堪,卻是文明的拓荒者,用腳步證明了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蘊(yùn)藏著無盡的礦產(chǎn)資源。1922年1月,他們成立了中國(guó)地質(zhì)學(xué)會(huì),并提交了4篇論文,8月就被吸納進(jìn)了國(guó)際地質(zhì)學(xué)會(huì)。中國(guó)地質(zhì)學(xué)的異軍突起給中國(guó)人在世界上帶來了尊嚴(yán)之光。
丁文江開創(chuàng)的田野工作方法成為中國(guó)地質(zhì)學(xué)界最寶貴的遺產(chǎn)之一。他一改中國(guó)文人自視高貴、輕視勞動(dòng)的舊習(xí),傳遞了一種吃苦耐勞的科學(xué)精神和研究方法。胡適盛贊他“這樣最不怕吃苦,又最有方法的現(xiàn)代徐霞客,才配做中國(guó)地質(zhì)學(xué)的開山大師”。這和我們新中國(guó)成立后地質(zhì)行業(yè)“以獻(xiàn)身地質(zhì)事業(yè)為榮、以艱苦奮斗為榮、以找礦立功為榮”的“三光榮”精神;“特別能吃苦、特別能戰(zhàn)斗、特別能忍耐、特別能奉獻(xiàn)”的“四特別”精神一脈相承。
我的外公是地質(zhì)隊(duì)的鉆機(jī)機(jī)長(zhǎng),他以鐵人王進(jìn)喜為榜樣,從不提地質(zhì)鉆探工作的辛苦,只是默默在野外奉獻(xiàn)了自己;我的母親參加過地質(zhì)隊(duì)的女子鉆機(jī),以瘦弱的肩膀扛過鉆桿,為山上施工的地質(zhì)隊(duì)員挑過熱騰騰的飯菜;我的父親是70年代西北大學(xué)地質(zhì)系的大學(xué)生,趕上了地質(zhì)行業(yè)最火熱的年代,他用青春與研究精神丈量了陜西秦嶺的各個(gè)礦脈,成為陜西地礦的地質(zhì)專家、全國(guó)勞動(dòng)模范,被業(yè)內(nèi)人士稱為“秦嶺活地圖”。成長(zhǎng)在這樣的地質(zhì)家庭,從小我就知道地質(zhì)人的辦公室在大山里,地質(zhì)人的心血成就與牽掛都在大山里。雖然現(xiàn)在單位從陜南遷到了關(guān)中平原,但至今只要我看到、走進(jìn)大山就會(huì)有回家的踏實(shí)感,和被親人擁抱的溫暖。《荒野上的大師》讓我聽到了跨越了一個(gè)世紀(jì)的召喚,讓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地質(zhì)人精神血脈的傳承。
《荒野上的大師》還原了一代中國(guó)科學(xué)人的科學(xué)探索歷程——將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的研究范式引入中國(guó),將實(shí)證精神植入學(xué)術(shù)傳統(tǒng)。100年前,丁文江在西南山區(qū)踏出的第一步開啟了中國(guó)科學(xué)人新世界的大門,這扇科學(xué)的魔法之門從此再未關(guān)閉。丁文江們?cè)诨囊爸胁ハ碌目茖W(xué)種子已經(jīng)長(zhǎng)成了蔥郁的密林,而根脈始終深植于那片他們一步步丈量過的土地。在知識(shí)獲取日益便捷的今天,這種“用腳做學(xué)問”的精神傳統(tǒng),也許是一劑喚醒學(xué)界、業(yè)界的良藥,需要我們珍視和薪火傳承。
(作者為陜西地礦綜合隊(duì)李文)